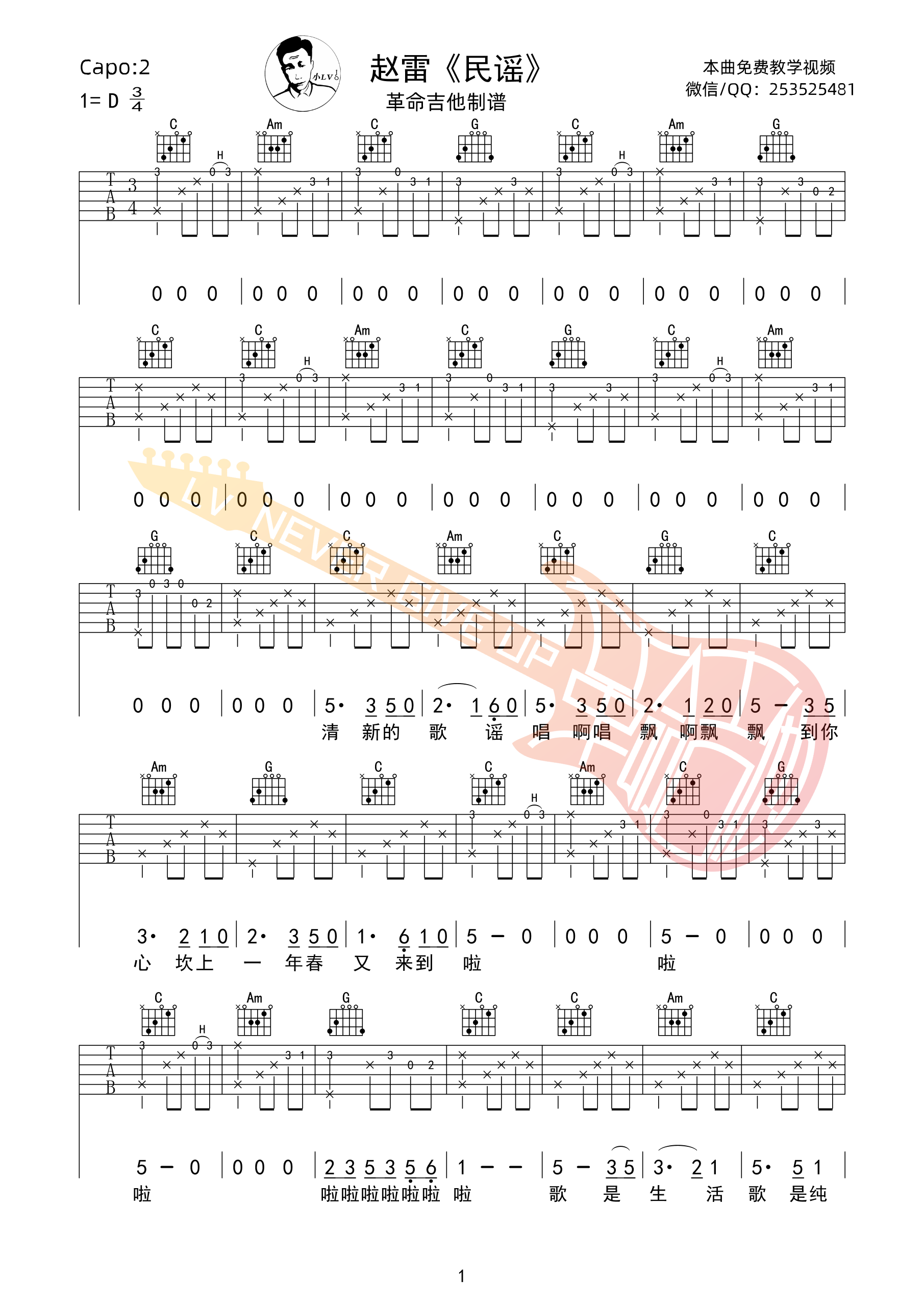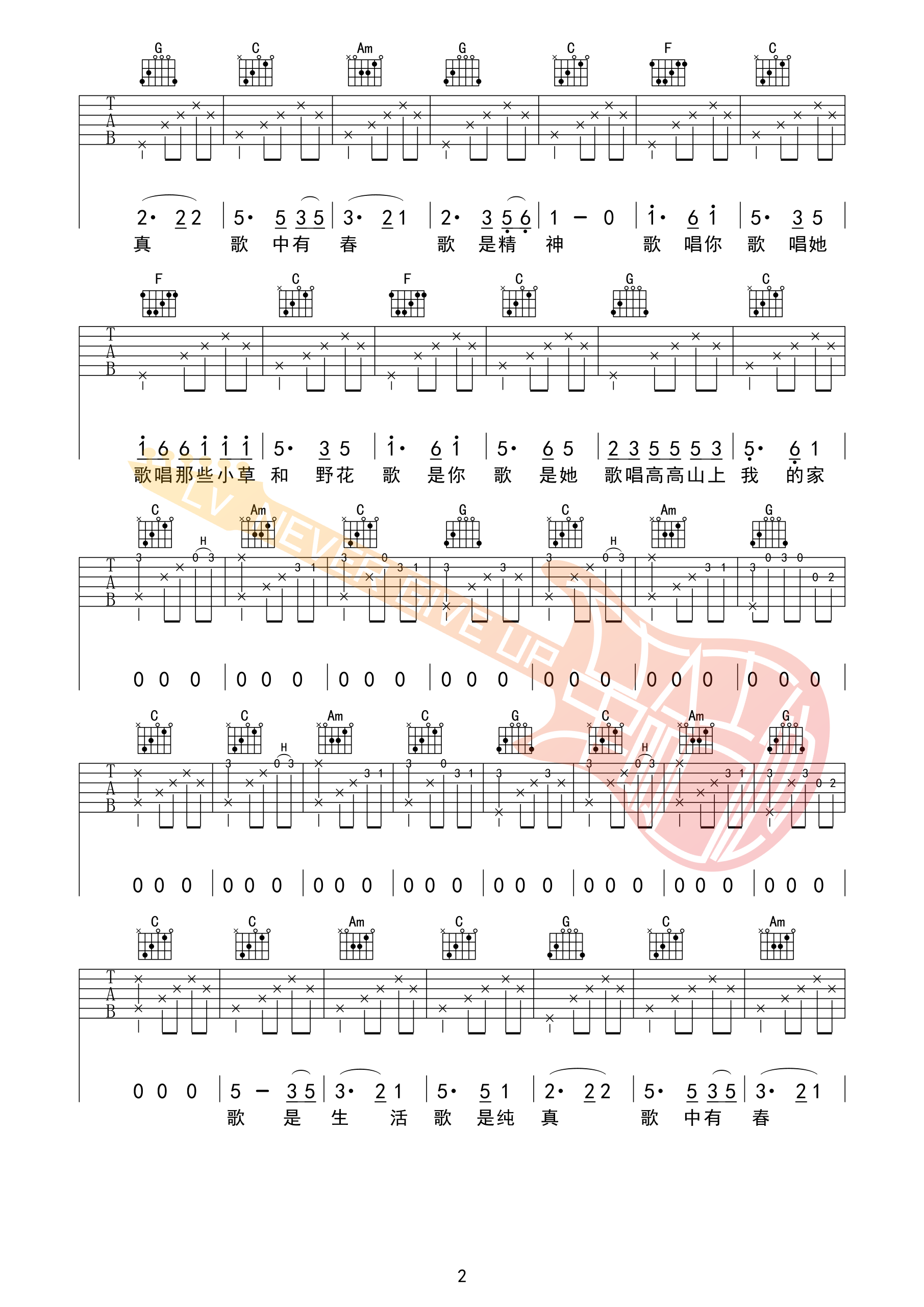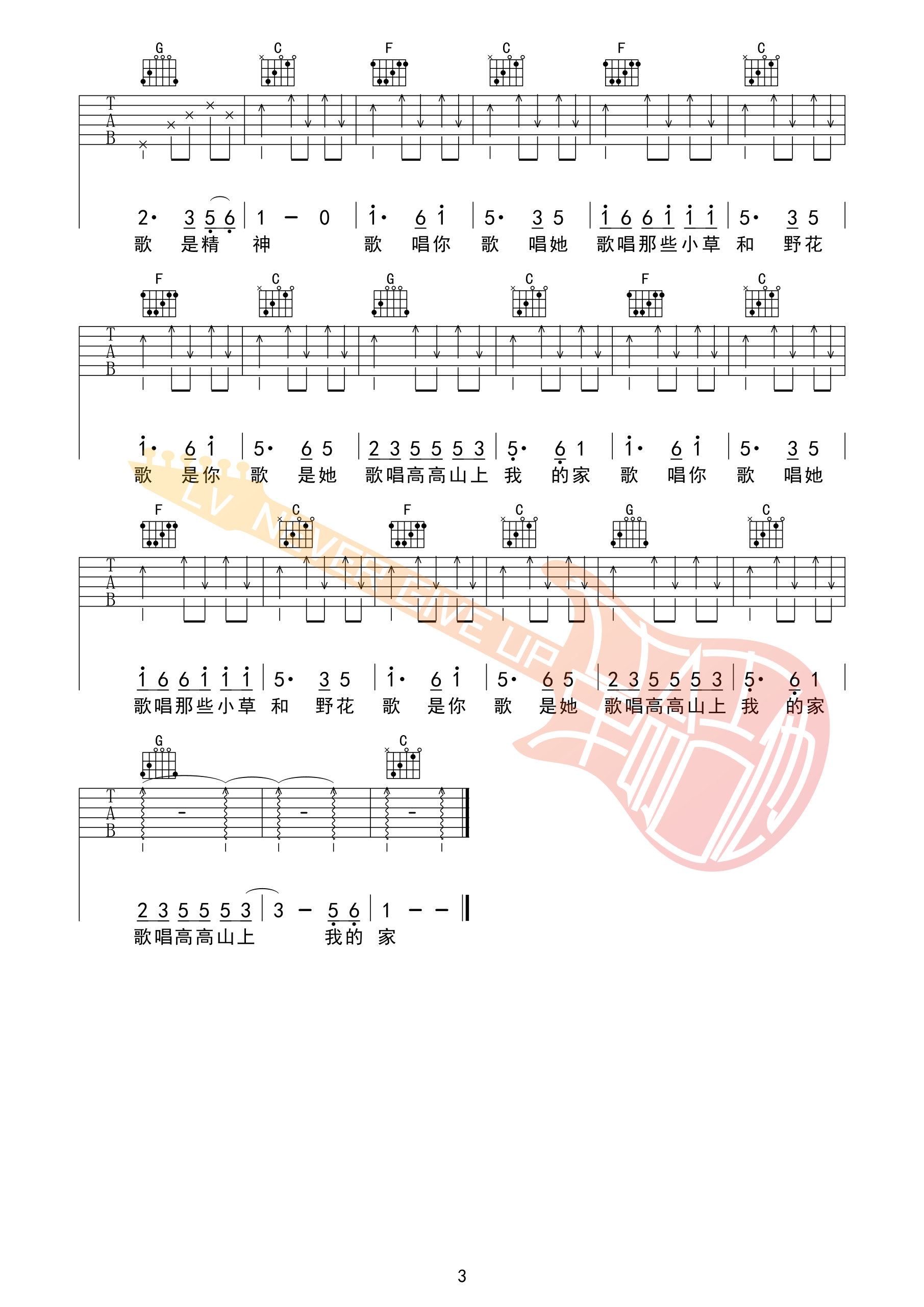《民谣》以质朴的语言勾勒出时光深处的市井图景,木质吉他弦振动的不仅是音符,更是岁月在泛黄墙面上剥落的细碎回响。歌词中反复出现的街角路灯、旧书摊与褪色车票,构建出流动的叙事空间,每个意象都是时代齿轮碾过的微小刻痕。三拍子节奏暗合火车行进般的律动,隐喻着人生无法停驻的单程旅途,而副歌部分突然升调的旋律转折,则暴露出平静叙述下汹涌的暗流——那些被压缩在旧皮箱里的未竟理想,始终在记忆夹层中窸窣作响。方言词汇的巧妙植入形成特殊的语言肌理,使地域性叙事获得超越地理坐标的普适共鸣,潮湿的南方雨季与干冷的北方站台在歌词中完成时空叠印。反复咏唱的"野菊花开了十八回"并非简单的岁月计数,而是用植物生长周期丈量灵魂的缩胀节奏,最终在尾奏渐弱的吉他泛音里,所有未言明的惆怅都化作月光下浮动的尘埃。这种创作刻意保持的粗糙质感,恰似老茶馆里说书人故意保留的喑哑声线,让故事本身的力量刺穿过于精致的表达外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