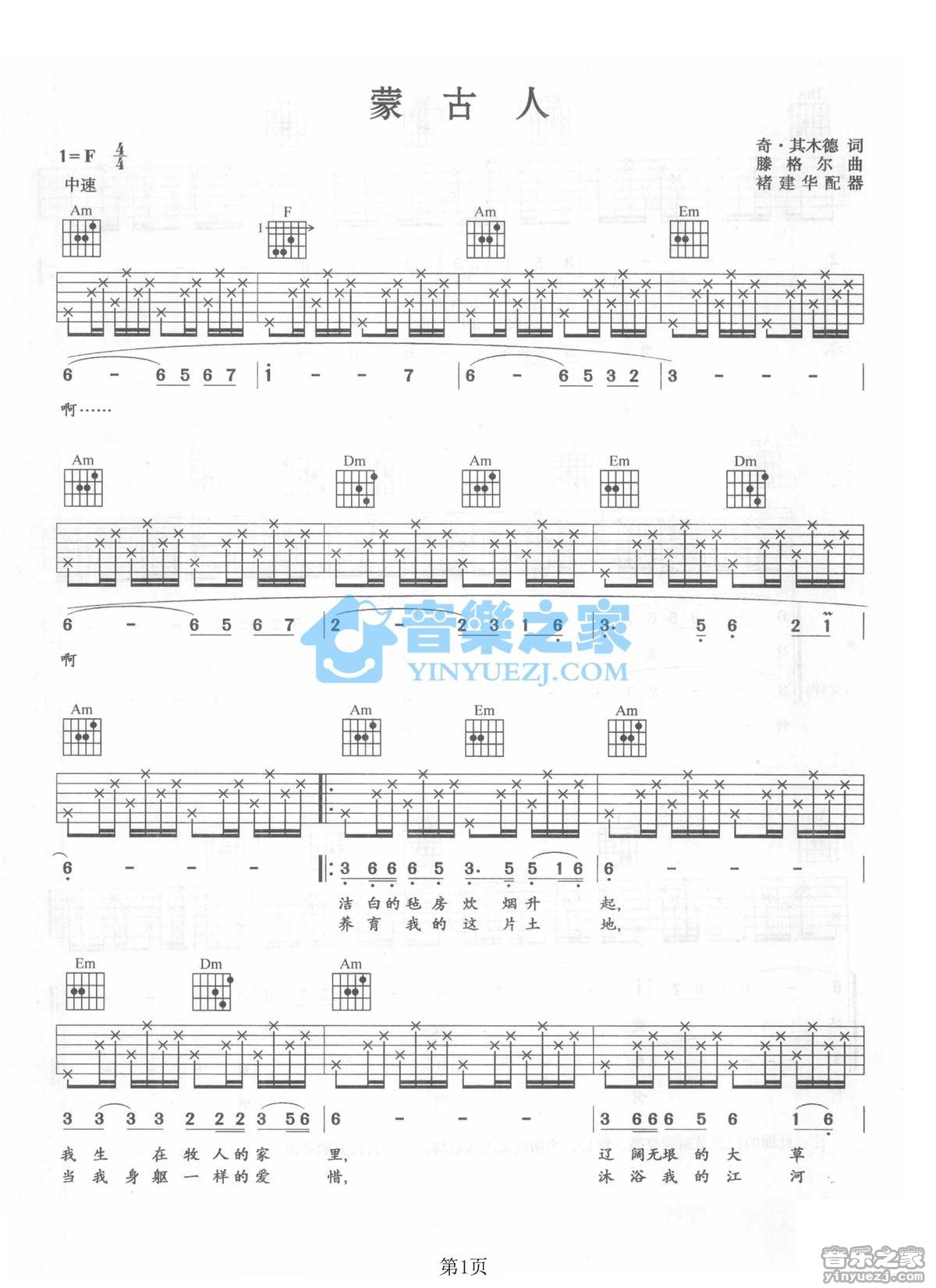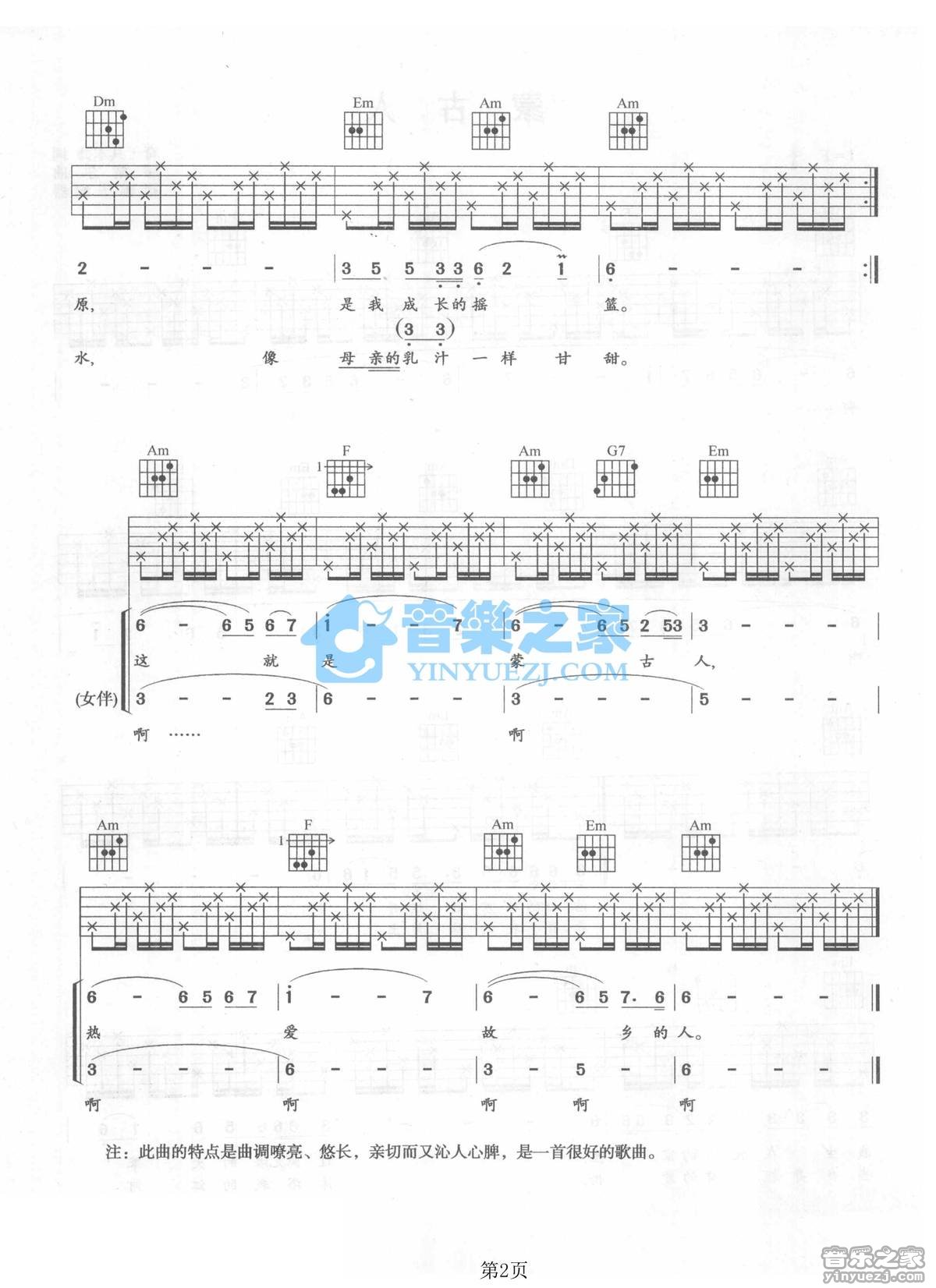《蒙古人》这首歌词以质朴而深情的笔触勾勒出蒙古民族的精神肖像,通过草原、骏马、苍狼等意象群构建起游牧文明的灵魂图腾。歌词中"长生天的子民"的自我定位,既是对萨满信仰的现代诠释,也暗含着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生态哲学。马头琴声与牧歌的意象交织,将听觉记忆转化为文化基因的传承密码,而"马蹄踏碎星辰"的壮阔画面则超越了时空限制,使游牧民族的迁徙史升华为永恒的宇宙诗篇。歌词中反复出现的火种意象具有双重象征:既是物理意义上的生存之火,更是文化血脉的延续之光。对敖包祭祀的隐晦指涉,透露出集体记忆与宗教仪式的现代困境,而"用烈酒浇灌荒原"的悖论式表达,实则暗喻着工业化浪潮下传统生活方式的悲壮抵抗。风蚀岩画与当代青年的并置,构成文明断层处的深刻诘问,最终在"把草原穿在身上"的隐喻中完成文化认同的当代表达。整首作品以现代汉语重构草原史诗,在蒙汉语境的互文性中,实现了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诗意对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