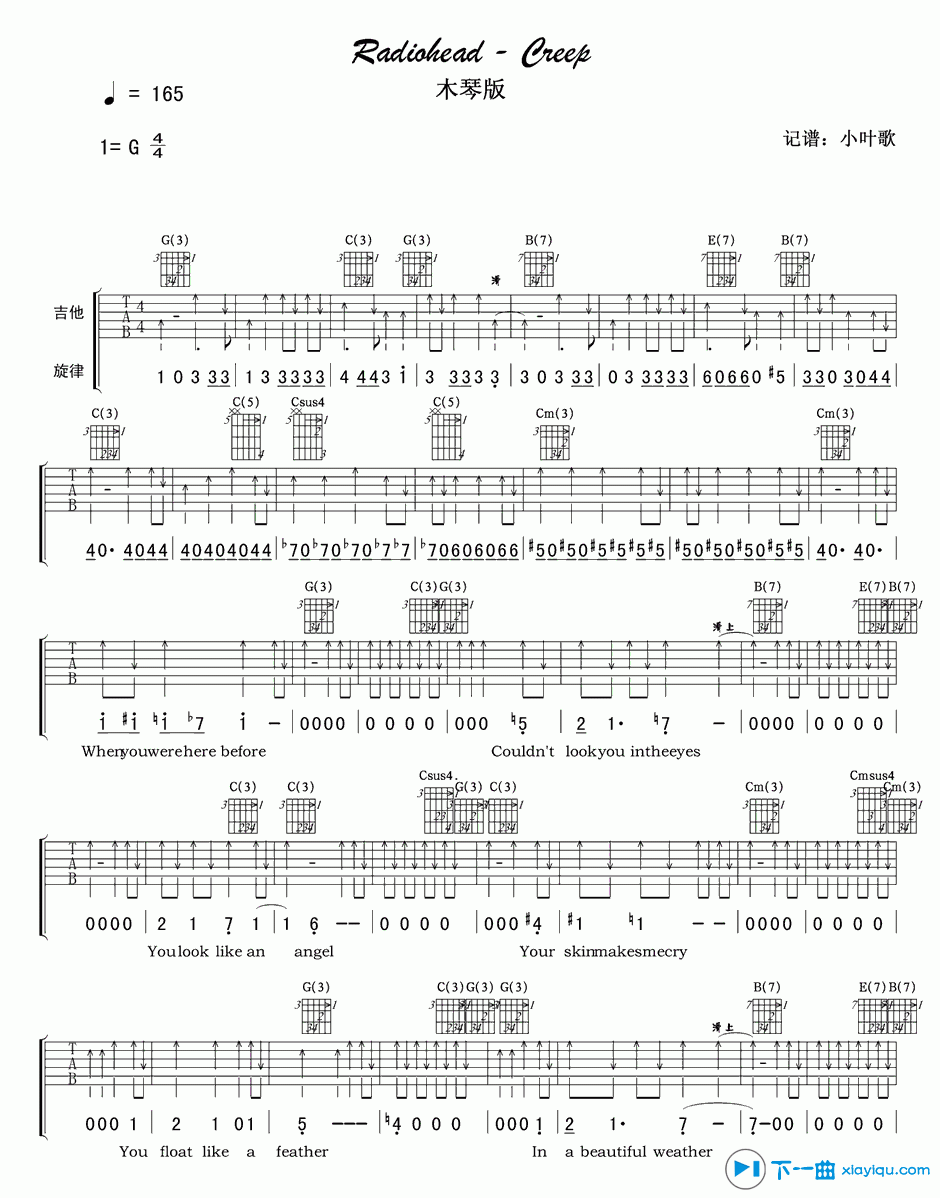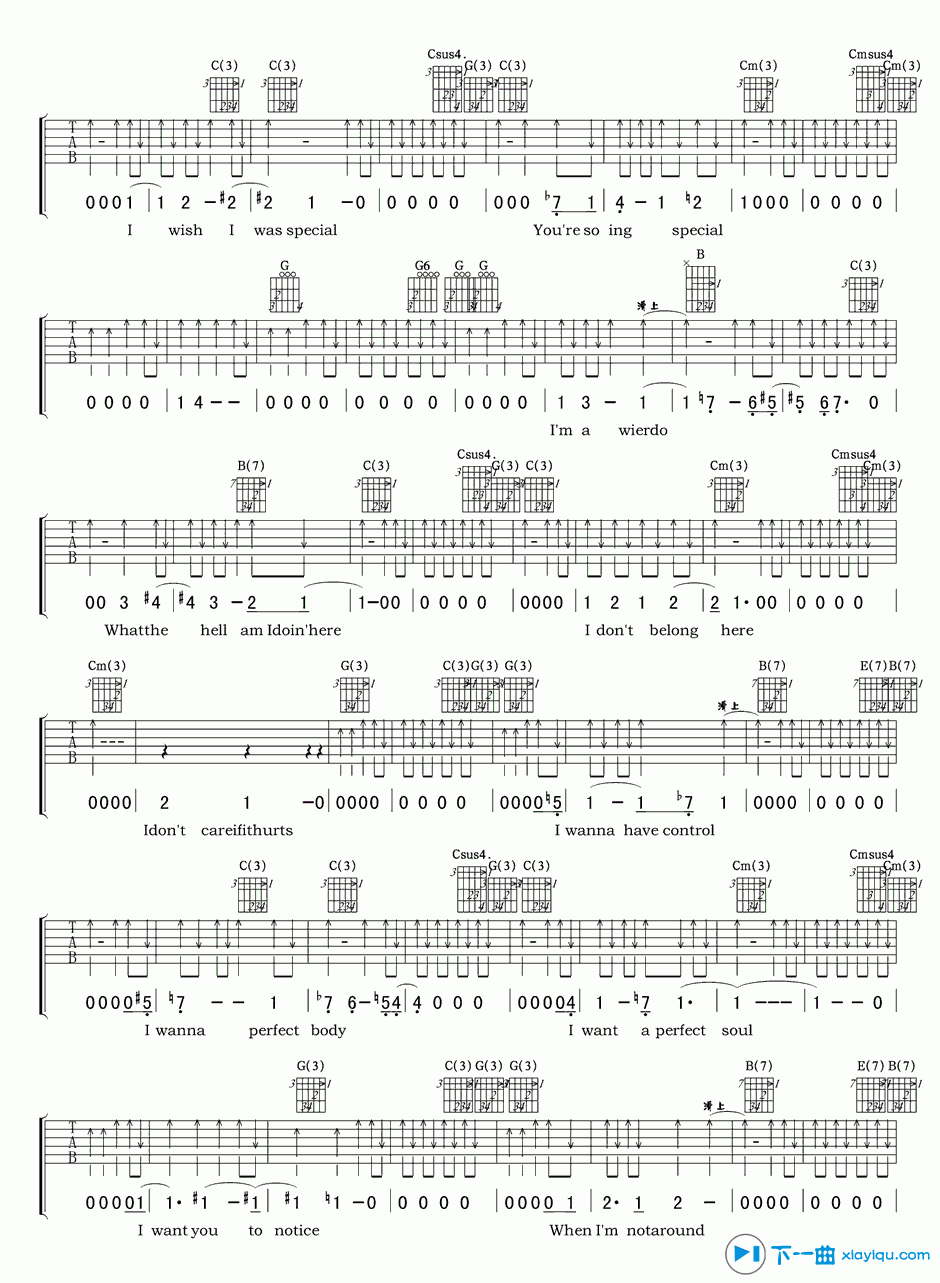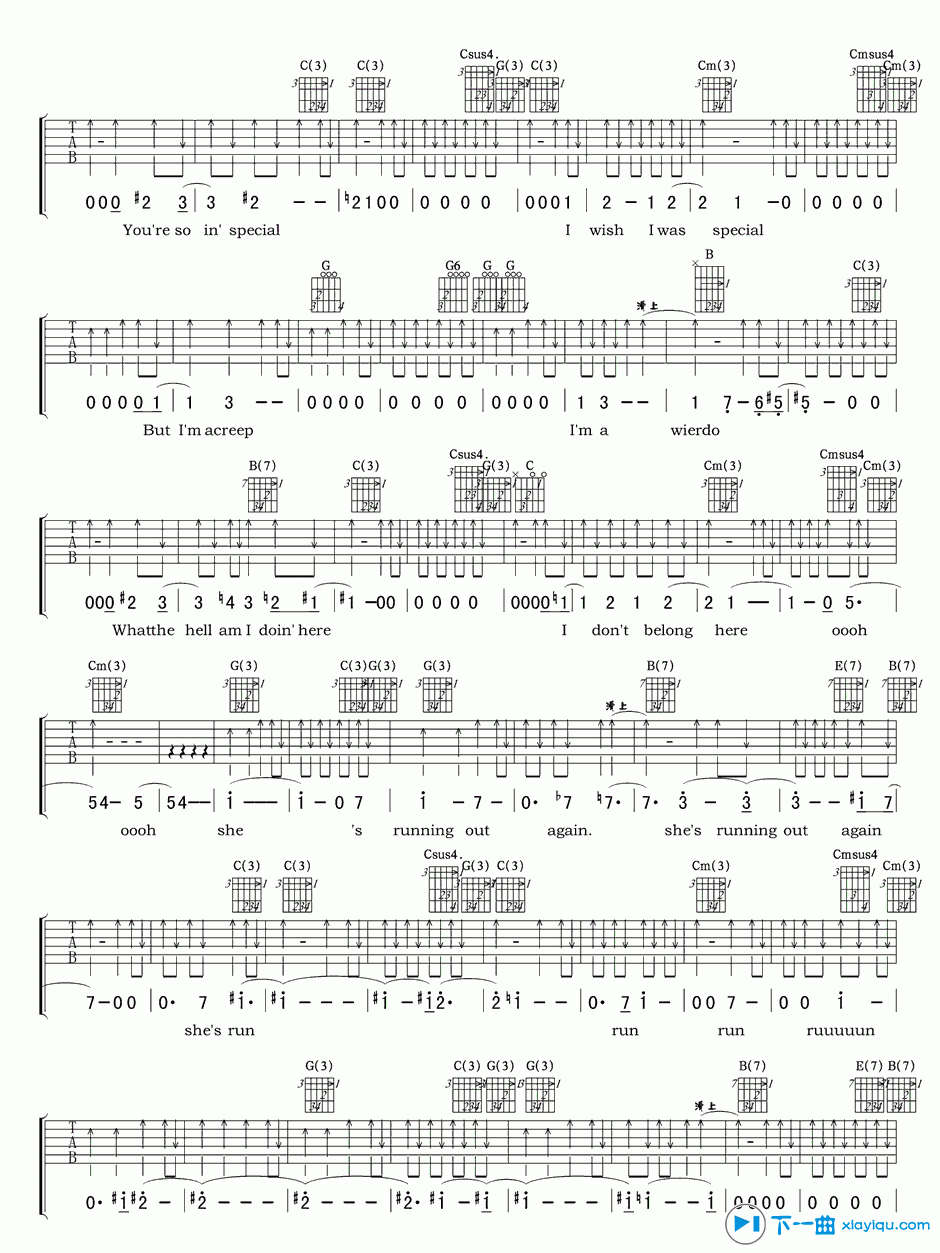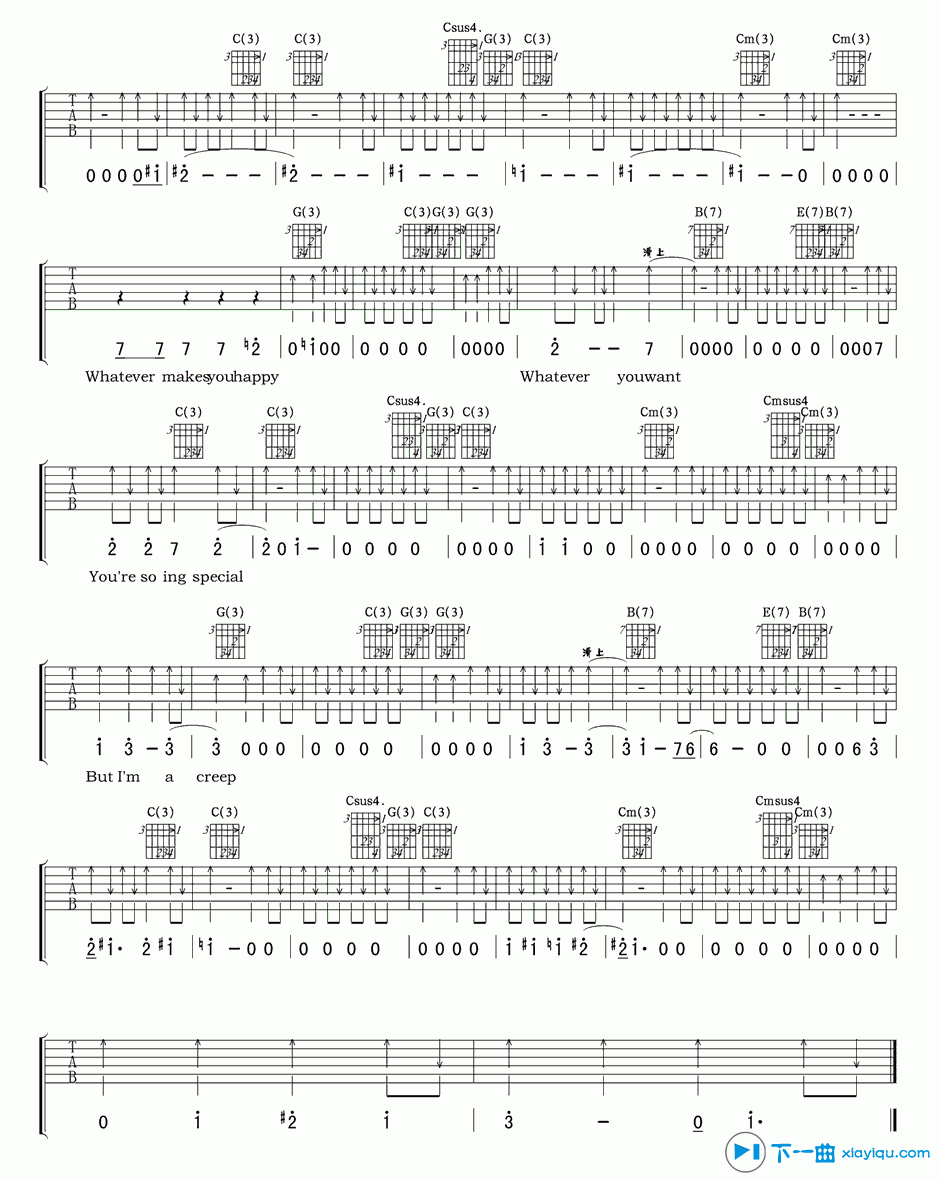《creep》以极具冲击力的自白式语言刻画了一个边缘者的精神困境,歌词中反复出现的"怪胎"意象成为整首歌的情感锚点。渴求与自我厌恶的激烈撕扯构成歌词的核心矛盾——"我想要完美的灵魂"与"我不配在这里"的反复咏叹,暴露出灵魂深处无法和解的裂痕。歌词通过具象化的身体描写(如塑料玩偶般的僵硬感)将精神异化转化为可触摸的生理体验,而"天使"与"蠕虫"的极端意象并置,则强化了主体在崇高向往与卑微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。监视器视角的"漂浮"意象暗示着现代人普遍存在的存在性眩晕,当歌词主角在玻璃窗外凝视理想化的"她"时,这种观察者姿态恰恰暴露了更深层的自我隔离。歌曲中不断强化的"特殊"与"平凡"的悖论,折射出当代身份认同的普遍焦虑:既恐惧被群体吞噬,又恐惧无法融入群体。最终那个爆裂般的高音质询"我在这里干什么",将存在主义式的荒诞感推向顶点,而歌词始终未给出解答的留白,恰恰成为每个现代倾听者自我投射的空白画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