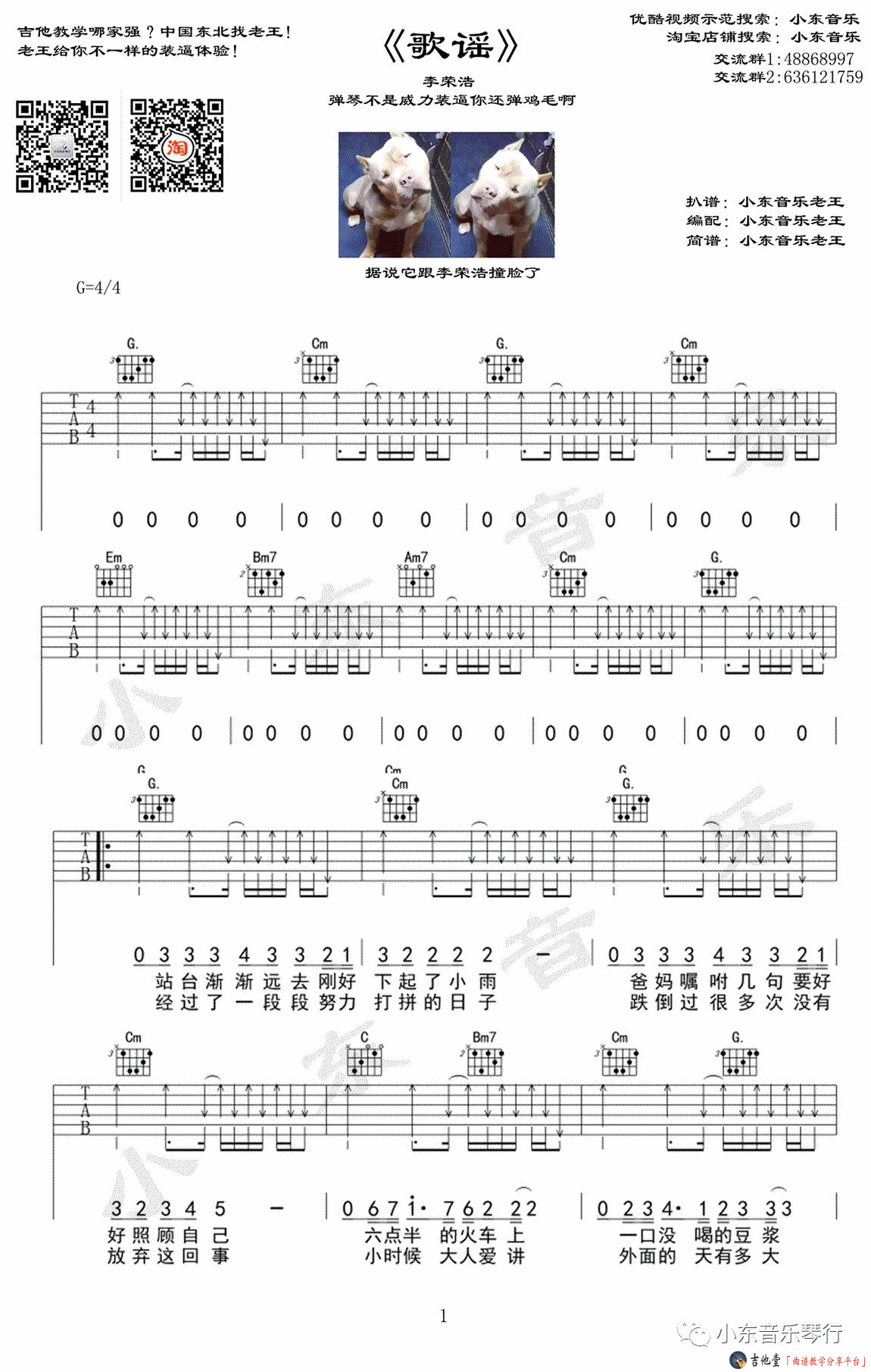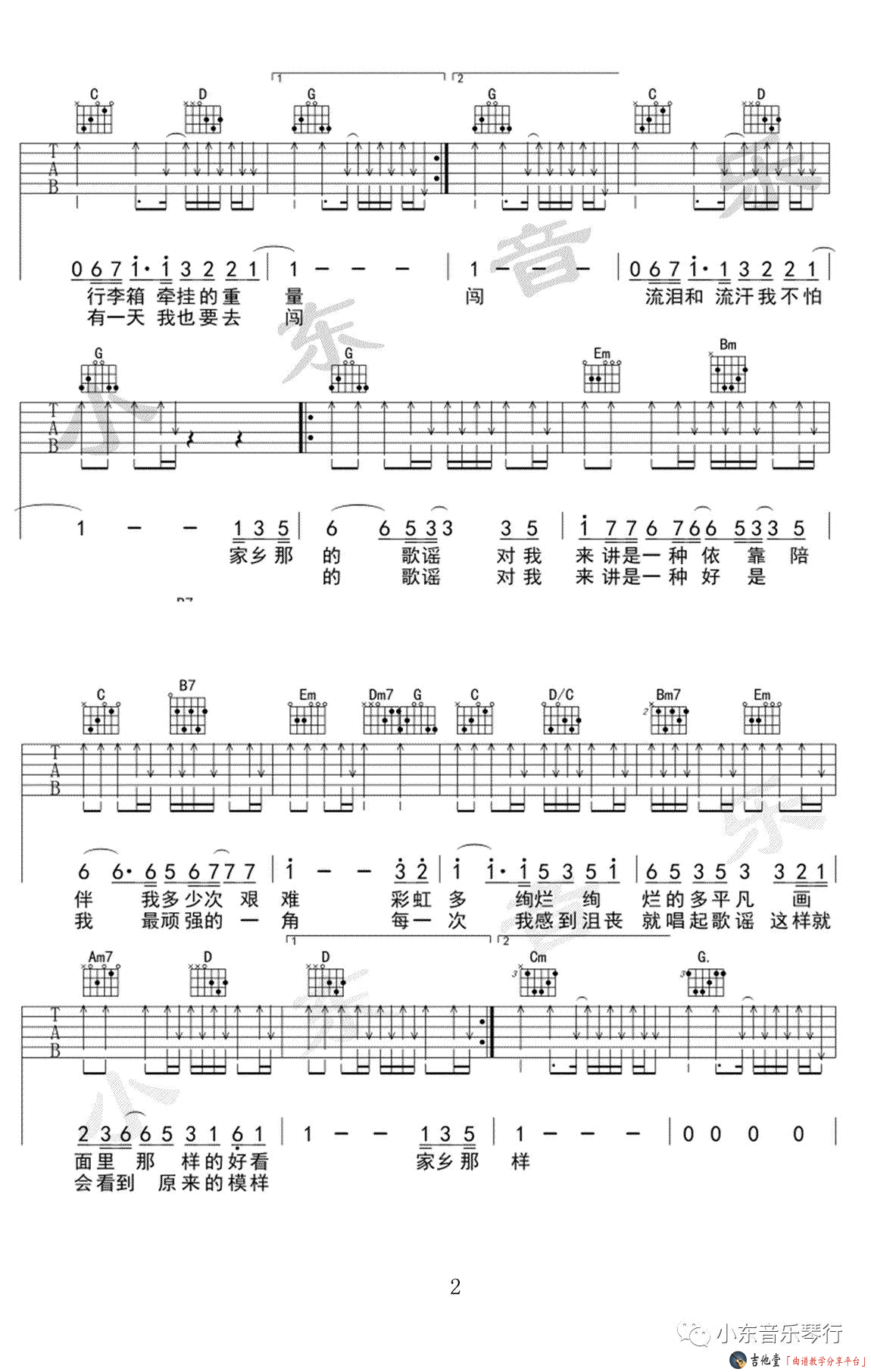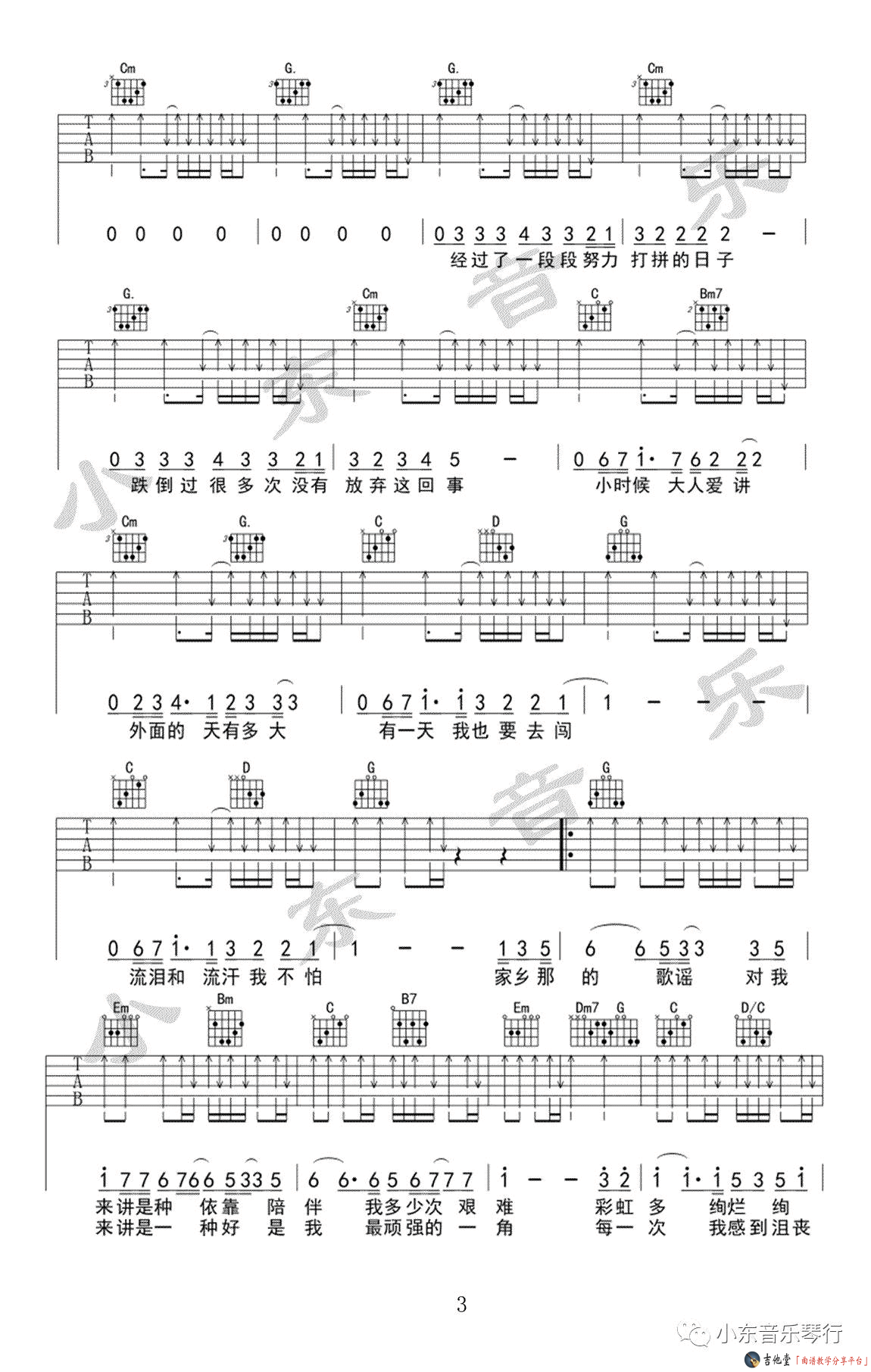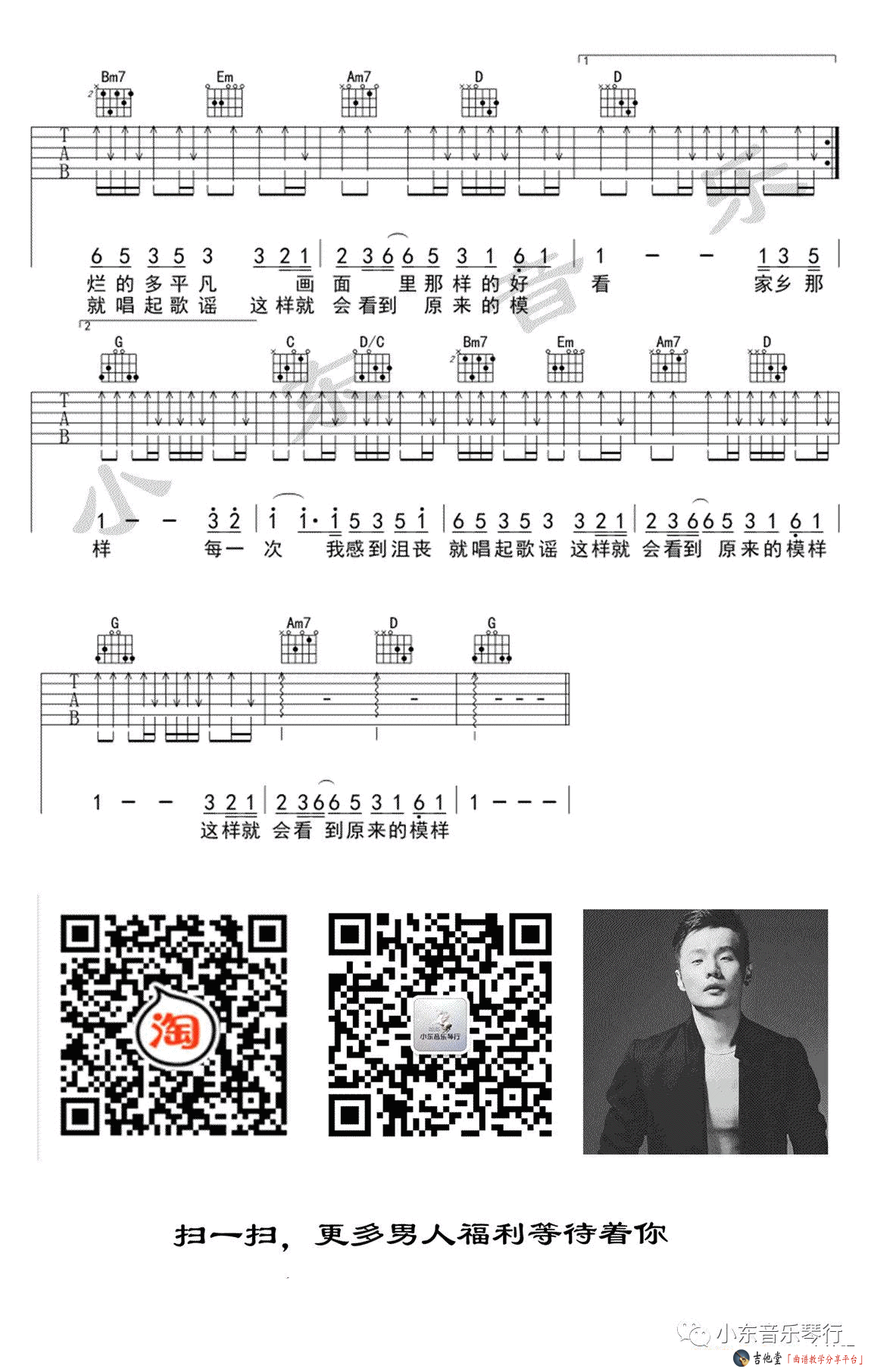《歌谣》以简洁质朴的语言勾勒出时光流转中的生命印记,将民间口耳相传的文艺形式升华为承载集体记忆的容器。歌词中反复出现的"传唱"意象形成时空回响,既暗示个体在岁月长河中的渺小,又彰显文化基因通过歌谣实现的永恒传承。那些散落在田野巷陌的旋律被赋予灵性,成为连接土地与心灵的脐带,记录着镰刀收割麦浪的沙沙声、溪水流过卵石的叮咚响,这些声音密码里藏着祖先的叹息与孩童的笑靥。四季轮回在歌词中化作不同的声部:春耕的号子带着泥土腥气,夏夜的童谣沾着露水清凉,秋收的鼓点震落枝头果实,冬炉边的低吟裹着柴火噼啪。创作者巧妙地将歌谣本体拟人化,使其具有行走山野的脚掌与收集故事的布袋,这种诗性转换让抽象的文化传承获得具象的生命力。当现代文明的机械轰鸣逐渐淹没乡野原声时,歌词里未完成的半句旋律恰似悬在屋檐下的风铃,提醒着城市化进程中那些正在消逝的声音档案。最终呈现的不只是对民间艺术的挽歌,更是对文化根系的无言守望。